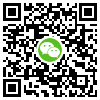医院的走廊里永远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,那是消毒水试图掩盖却欲盖弥彰的焦虑味。
作为一名处理过不下百起医疗纠纷的律师,我见过太多这种场景:手术室的灯灭了,医生走出来,原本是宣告“手术成功”的时刻,却因为患者未能如预期般苏醒,或者某个肢体失去了知觉,瞬间变成了修罗场。
今天我想聊的这个案子,并不血腥,却极具代表性。它像一把手术刀,精准地切开了医疗法律中最模糊、也最令人纠结的那个横切面——并发症与医疗过错的边界,以及签字是否就代表了真正的知情。
一场“成功”的手术,一个瘫痪的结局
案子的主角是65岁的赵老先生。因为严重的腰椎管狭窄压迫神经,他连走路都成了奢望。在当地一家三甲医院,骨科主任建议进行“后路腰椎椎管减压植骨融合内固定术”。
这在骨科算是常规的大手术,但也并非罕见。术前谈话时,医生拿出一沓厚厚的《手术知情同意书》,上面密密麻麻列举了二十多条风险,包括但不限于出血、感染、脑脊液漏、甚至瘫痪。赵老先生的儿子在上面签了字。
手术过程记录显示一切顺利。然而,术后麻醉消退,赵老先生却发现原本只是疼痛的右腿完全不能动了,且伴有大小便失禁。
家属的天塌了。
医生解释这是“马尾神经损伤”,是手术的已知并发症,发生率虽低,但确实存在。家属则认为:好端端走着进去(虽然疼),现在却瘫着出来,这一定是医生手抖了,切坏了神经。
愤怒的家属封存了病历,将医院告上了法庭,索赔120万元。
法律的审视:结果不好,就是医生的错吗?
在非法律人士的朴素价值观里,结果正义往往等同于程序正义——“我花了钱,挨了刀,结果更坏了,你医院就得负责。”
但在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的框架下,医疗损害责任适用的是过错责任原则。也就是说,患者要想拿到赔偿,必须证明三个点:第一,医院有诊疗行为;第二,患者有了损害后果;第三——也是最难的一点——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,且这个过错与损害后果之间有因果关系。
在这个案子里,损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。但“过错”在哪里?
这就引出了医疗纠纷中最核心的博弈点:医疗鉴定。
在法庭的主持下,案件移送至医学会进行鉴定。鉴定的核心在于区分这是“医疗技术过失”还是“难以避免的并发症”。
如果是技术过失,比如螺钉打偏了直接刺入椎管,或者止血不彻底导致血肿压迫神经,那就是实打实的医疗事故(或医疗损害),医院必须赔。但在赵老先生的案子里,术后影像学检查显示,螺钉位置完美,减压也很充分。
那么,神经为什么会损伤?
鉴定专家指出,对于长期受压的神经,在突然解除压迫后,可能会出现“缺血再灌注损伤”。这就好比一个人在雪地里冻僵了手,突然放进热水里,反而会坏死。这在医学上属于难以完全预料和防范的并发症。
如果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,医院似乎要胜诉了。毕竟,医学不是神学,医生治不好病并不天然构成犯罪。
逆转的关键:那张签了字的纸
然而,作为患方律师,我们在庭审中抓住了另一个常常被忽视的法律武器——违反告知义务。
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二百一十九条规定得非常明确: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。需要实施手术、特殊检查、特殊治疗的,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具体说明医疗风险、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,并取得其明确同意。
请注意,“说明”和“签字”是两码事。
我们在庭审中反复盘问主刀医生一个细节:“在术前谈话时,您是否针对赵老先生这种长期压迫、神经极其脆弱的高龄患者,特别强调了缺血再灌注损伤导致瘫痪的具体概率?还是说,您只是把那张印好的、通用的风险告知书递给家属,指着‘瘫痪’两个字让他们签了个字?”
医生沉默了。由于日常工作繁忙,很多医生确实将“知情同意”异化为了“签字画押”的行政流程。
在庭审录音和笔录中显示,医生当时的表述更倾向于:“这个手术风险不大,我们做得很多,签字主要是走个流程。”
正是这句话,成为了逆转的关键。
法院最终认定:虽然医院在手术操作技术上没有明显违规,但在伦理过错和告知义务上存在瑕疵。患者享有知情同意权,这个“知情”必须是实质性的。如果赵老先生知道这次手术有这么高的瘫痪风险,他可能会选择保守治疗,哪怕忍受疼痛,也不至于瘫痪在床。剥夺了患者选择“不手术”的机会,这就是侵权。
判决背后的法理温情与冷峻
最终,法院判决医院承担30%的次要责任,赔偿约40万元。
这个判决结果让双方都不太满意,但却极具法理标本意义。
它告诉医生:技术无错不代表法律无责。医学充满不确定性,法律允许并发症的存在,但不允许你傲慢地替患者做主,或者轻描淡写地掩盖风险。
它也告诉患者:医疗不是消费。不是所有的痛苦都能换算成金钱。医院承担的是30%的责任,意味着另外70%的苦难,赵老先生需要自己由身体来承担。这是生命科学残酷的一面。
结语:信任是比法律更昂贵的契约
在这个案子结束后,赵老先生的儿子曾问我:“律师,如果当初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,有可能会瘫痪,我还会让我爸做这个手术吗?”
他自己也没有答案。
医疗损害责任纠纷的法律条文冷冰冰地躺在法典里,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到一千二百二十八条,字字珠玑,界定了过错、病历管理、免责事由。但在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里,法律能做的只是事后的救济和止损。
真正的防线,其实在手术室门外的那次谈话里。
当医生不再把告知书当成“免责金牌”,而是当成与患者共担风险的契约;当患者不再把医学当成万能的商品,而是理解其局限性。或许,法庭上这种令人心碎的博弈才会少一些。
毕竟,在柳叶刀下,医生和患者本该是战友,而不是被告席两端的敌人。